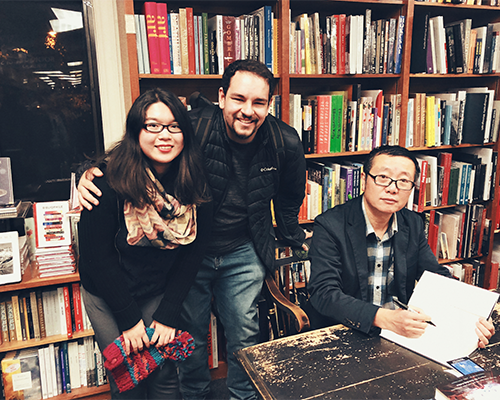
这俩家伙都太能扯了吧!
本来想全翻的结果还是放弃了一些P2里的闲扯淡
TM: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
刘:科幻小说的起源在西方,中国传统文学和社会主义结构都没有类似于科幻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相关。
TM:资本主义世界重视金钱,而社会主义对美好未来有更多的期许,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否影响了中国的科幻?
刘:资本主义确实是建立在金钱主义和享乐主义之上的,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去设想未来。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正是在三十到六十年代的欧洲和美国,未来主义思想的发展也远远早于以《理想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于未来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社会主义相信未来是光明美好的,资本主义原先也这么相信着,只是后来意识到某些负面因素会对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TM:你第一次接触科幻是什么时候?
刘:第一次读科幻是在十岁的时候,当时刚开始读凡尔纳。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幻还是个很新的东西。那本书在五十年代被印刷出版,我父亲买下之后就藏在床底下。这书后来就被禁了。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的中国有一场精彩的文化运动,当时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科幻都被大规模引进。虽然在之后的文革中很多作品都被禁了,部分五十年代引入的作品还是在私下里被流通,我也是这样才接触到西方文化的。
TM: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读科幻的感受么?
刘:科幻很有意思。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凡尔纳的风格偏现实,让我觉得那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故事。后来我的父亲告诉我那一切都是基于科学的幻想。我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的感受和梦想都在书中被表达出来,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个比我原先狭窄闭塞的世界要宽广很多的新世界。莫言那本叫《透明的红萝卜》的书中就讲述了那些和我一样在那个年代成长的孩子们是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并在最后得以释放和爆发。
TM: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创作自己的科幻故事?
刘:在机缘巧合读了凡尔纳之后,我很久都没有再读到类似的书,唯一能读到的只有前苏联的科幻文学。事实上,很多的当代作品直到七十年代后才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对我影响很深的一部是《2001太空漫游》,正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我才开始在1981年动笔写作,这让我初尝了科幻的神奇力量。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于宇宙的敬畏都让我很受启发。
TM:硬核科幻美在哪里?
刘:最美也最有力量的故事并不是由作家创作的,最好的故事就是科学本身。而科学的美只存在于数学公式之中,并不能被普通大众所欣赏,于是科幻作品的使命就是通过文学展示其中的部分美丽。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写作的风格,别人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我并不过分感兴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更喜欢研究人类和宇宙空间的关系。
TM:在你所有的作品中, 人类都在试图逃出被灭绝的命运。为什么你的作品总是在谈论宿命论?
刘: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相反,我相信未来是难以预测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会在某一个时刻遇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需要讨论的并不是人类将被如何灭绝,而是如何从灾难中幸存——这也是科幻中一个常见的主题。自从人类文明出现后我们尚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毁灭性的打击,唯一两次接近毁灭,一次是十四世纪的鼠疫,一次是北约和华约之间差点发展成战争的核争端。这些实际上也并没有那么的灾难性。不过我们在未来是一定会遇到真的灾难的。
TM:你在书中常常提到逃亡主义。你是否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解决灾难的方式?
刘:我的书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探索可能性,毕竟我们的主流信仰和社会价值并不适合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人类文明想要生存,我们曾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譬如人权、民主等等,都需要被重新审视。我们固然可以选择坚守着这些价值观直到灭亡,但这并不是个聪明的决定。
TM:你现在还在做工程师的工作么?
刘:我之前工作的电站在09年因为环境污染被关了,所以我只能另谋生路。北京的环境污染终于让我变成了无业游民啊,哈哈。我现在在全职写作。
TM:你有没有告诉你的父母你现在是全职作家呢?还是你把这个当做个秘密?
刘:对我的父母我没有必要去隐瞒什么。不过他们对于这些也并不关心。大家都觉得科幻是写给小孩子看的,没有人把这个当真。在美国观点就很不同了。美国的科幻读者都是四五十岁,很少有小孩子读科幻的。
TM:从你的作品中产生了这么多的周边文化,你是否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标签?
刘: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都没有什么人读科幻。《三体》出版后,媒体和公众都开始更加关注科幻文学。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转变。
TM:你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一般做什么解压?比如说在你准备下一本新书发布的时候。
刘:对于这种事我一般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我知道一本书的成功,跟运气、时机都很有关系。我知道我的下一本书可能不像《三体》一样成功,所以也并不太在意。
TM:有传言说亚马逊出资十亿要拍《三体》的电视剧,也又听说电影也正在拍摄中。为什么一部电影要花这么长时间来制作?
刘:我并不了解关于亚马逊出资的事。我早就把《三体》的改编权转手了,所以也没有参与到任何的制作过程中。电影的制作我确实是有参与,我认为制作时间之长是因为中国并没有经验来拍摄这种大规模的科幻电影。电影直到现在还在后期中。
TM:你和电影导演的关系密切吗?就像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的原作者)和库布里克那样?
刘:据我所知克拉克和库布里克之间其实一直都是有一种矛盾存在的,我和导演的关系也是这样。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没有办法避免。作者总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去想问题,不是总想导演和制片人那样要考虑更多现实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不要让作者参与电影的制作中。打个比方说,另一部由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就要公映了,在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导演和制作团队完全没有让我介入创作过程,甚至不理会我的来电,但制作过程却十分顺利。就算在拍摄科幻电影经验丰富的美国,经典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更别提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尝试了。我们当然可以去和好莱坞的团队进行合作,但是没有来自中国的好的管理团队,这个合作会变得很困难。
TM:你有预料到自己的作品会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吗?以及你的作品是针对中国读者而写的么?
刘:百分之百是为了中国读者而创作的。别提国际影响力,就算在国内我也没有预料到这部作品会受到如此大的欢迎。
TM:听说你的妻子和女儿都不读你写的书?
刘:科幻读者是一群有奇怪品位的人,我的妻子女儿不在其中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也并不期望她们喜欢这类作品。科幻迷们和大多数的读者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打个比方说,很多科幻作品的文学价值很低,却不妨碍它们成为经典,这正是因为科幻读者在乎的东西远远超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本身。
TM:你作品之所以在国际上都大受成功,是不是很大程度收到了奥巴马评价的影响?
刘:事实上《三体》在奥巴马读到之前就已经很流行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读到它。说他大大地推广了这本书倒是真的。在奥巴马推荐了这书之后,它的排名一下从亚马逊的三千多升到了一百以内。
TM: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如何发现这本书的,以及他为什么如何喜欢它?
刘:他并没告诉我这些。我们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只做了很简短的交流,他的周围又全是警卫。我们聊了我们各自的女儿都正好要升入大学,他对于我女儿要去学机械感到很惊讶,我猜这是因为这个专业在美国很少见的原因。除此之外,他就说了我的作品会成为一部经典。至于把他的评价印在书封上只不过是营销手段而已了。
TM:你是如何有动力在就算没有酬劳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写作呢?
刘:没有名气、没有稿费、又没有人注意你,这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常态。像现在这样成名了反而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在以前写作就算是一种本能,作为科幻迷的我只不过是想要分享我的想象和热情,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没有动力创作的。我们就像球迷一样。不过现在当写作成为我的本职之后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有时候会让人心力交瘁。《三体》的畅销带来了各个方面的问题,电影的审核以及营销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TM:你能够在书中批判政府,但是在现实中却不能够,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刘:在书中提到文革并不算是对政府的批判。当今政府对文革其实也并没有很正面的评价,所以我的观点并谈不上出格。而中国政府其实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愿过多提及它。《三体》发行的时候正值文革三十周年,为了避免通不过审核,我们把关于文革的那一段从书的最开头挪到了中间的部分,我猜他们在审书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那一段。
TM:对于人类试图与外星文明进行沟通,你怎么看?
刘:我们在宇宙中是很寂寞的,这也正是人类的本能去在外星中探索生命。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我们不能想当然去觉得我们的法则在宇宙中也能通用,也不能想当然觉得外星人一定是有好的。我们应该去多听、多观察,而不是贸然和他们建立联系或者暴露自己的宇宙坐标。
TM:你的作品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有被误解的地方么?
刘:翻译的问题在主流文学中很常见,但对于科幻作品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学的是工程,我的语言也很简单。说实话英文的译本比我本身写得要好很多,我会建议会读双语的人都去读英语的版本。科幻作品其实很容易翻译成英文,毕竟这其中的核心概念和写作方式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翻译的过程也只不过是把它们还原成本来的语境。
TM:你未来的理想是什么?
刘:接着写科幻小说。下一本我要写的东西会和《三体》很不一样。
TM:克拉克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你的作品也在影响新的这一代。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刘:我确实借由这种边缘的文学形式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我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毕竟和中国主流科幻相比,我的作品还是偏小众。中国很多的科幻作家都效仿美国的风格,喜欢自我反观人类的内心世界。美国的科幻对于探索宇宙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这和我喜欢写的东西很不一样。中国已经诞生了两位获得雨果奖的作家,也因此很多科幻小说家都在试图步他们的后尘去仿照美国的科幻风格写作,就算这种风潮在美国已经慢慢退去了。我觉得这种趋势并不好。
TM:《黑暗森林》中描写的更像是现实,你只是加了一点点科幻的元素进去而已。
刘:中国读者喜欢读根源于现实的作品,从现实中走进一个幻想的世界。这也是我的写作风格。
TM:你更喜欢《星际迷航》还是《星球大战》?
刘:《星际迷航》。星战其实更多的还是幻想。《星际迷航》用的是31世纪的科技来讲述31世纪前的故事。
TM:写作科幻是为了预测未来吗?
刘:真实的未来是无法被预测的。科幻只是为未来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去预测未来。在这各种各样的对于未来的猜测中,总有一些会成真的。
TM:你对于21世纪的看法如何?是乐观还是悲观?
刘:乐观主义在科幻创作中已经消失很久了。不过相比于其他的中国作者而言,我还是更偏向于乐观主义。我相信只要人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未来一定还是光明的。
TM:为什么在你的作品中女性角色总是如此虚弱?
刘:性别在我的书中其实并不重要。我的角色只不过是用来讲述故事的工具而已。就比如说《三体》第三部中的程心,在我本来的设定中她是一个男性角色,但是编辑站在平衡角色的立场上将她改成了女人。
TM:你似乎对于电脑游戏很痴迷,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刘: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就是中庸。我在学校的时候从来没有被人欺负过,成长的过程也比较平凡,一直循规蹈矩。在文革期间我的家庭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对我的影响也都是有限的。不像其他作家,我从来不觉得现实残酷,也没有面对过很大的挫折。但这也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有点无趣和狭隘。所以对我来说,写作科幻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拓展我对世界的理解。
TM:你怎么看《我的三体》?(Minecraft动画版三体)
刘:我不喜欢,里面的人脸都变形了。
TM:你是个冲动型的作家还是喜欢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再写作?
刘:我特别喜欢计划,甚至都有点极端。之前我没有很多时间只能兼职写作,而现在计划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我写作的时候就像是一台精准的打印机,我会在写字之前把要写的一切细节都在脑海中构想好。
TM:你在《三体》电影的制作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
刘:我参与了脚本的写作和3D特效的概念构思,但我也只是提供了一些建议而已。